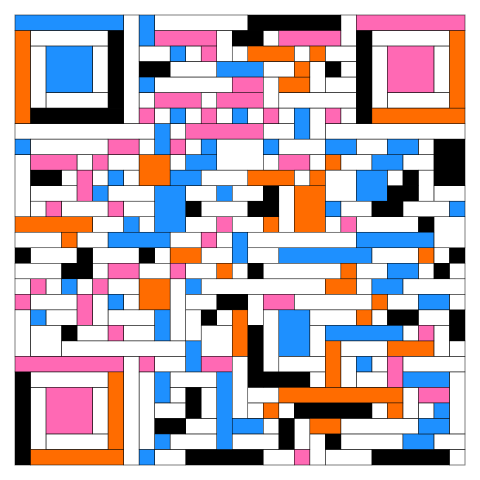《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網絡爆火后,快遞員胡安焉首部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遞》近日出版,記錄了一個快遞小哥平凡崗位的成長歷程,真誠感人,令人淚目。

北京市通州區高樓金小區總共有16棟樓,其中1號樓到7號樓住的是回遷村民,8號樓到16號樓是外來的租客。回遷樓的快件都很好送,他們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買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門邊或水電井里。
因為村民們彼此熟識,鄰里間會互相關照,連貼小廣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樓里的老人逮住。相對地,租客住的幾棟樓就魚龍混雜,他們大多是北漂的年輕人,有的還是合租戶,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沒有人了。住戶之間彼此不認識,樓里進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丟失。
| 01一半穩定一半老換人
我剛到高樓金的時候,同組的一個同事就讓我送8號樓到16號樓,他自己送1號樓到7號樓。于是我每天送半個高樓金、一個新城樂居,加影視城工地,三個分開的地方來回跑,經常疲于奔命、氣急敗壞。
漸漸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里。我發現小區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
剛來的時候,誰都是從最爛的小區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沒走。沒走的人可能會換到好一點兒的小區,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區的人會長久留下來,剩下不好送的小區就讓新人去送。新人剛來時一般都不會太計較,但逐漸地就會察覺到其中的不公平。
這種心態的轉變一般只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短。假如遲遲沒有改變的機會,新人就會離開。于是小組里總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動,另一半的人卻換個不停。
其實在當時我就已經察覺到,工作中的處境正在一點點地改變我,令我變得更急躁、易怒,更沒有責任心,總之做不到原本我對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這些改變有時會讓我覺得痛快,我痛快的時候就不太能感覺到煩躁和不滿。
比如有次我罵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我很少罵人,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平常我們在小區里送貨,一般離開三輪車時都不會拔下鑰匙,因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鑰匙很浪費時間,也沒有實際意義,小區里沒人會偷快遞車。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樓,才剛走到二樓,無意中朝樓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把她三歲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駕駛座上玩耍。
娃娃的雙手扶在了車把上,模仿在開車的樣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輕輕一擰,車就真的會往前沖出去——我嚇得趕緊撂下快件往樓下跑。當時我組里的一個同事,因為上樓時忘拉手剎,三輪車被大風刮跑了,蹭到了旁邊的一輛小轎車,最后賠了1600元。
我不敢想象一個小娃娃啟動了我的三輪車會造成什么破壞和傷害——他可能會撞到停在前面的轎車,那是我賠不起的,也可能會剮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從車座上摔下來,被車輪碾過……想到這里我幾乎要眼前一黑了。
我很生氣地罵了那個婦女,她只訕訕地看著我,我還記得我說她:“小孩子不懂事,難道大人也不懂事嗎?!”——這其實是我在葛優主演的一部電影里聽來的臺詞。
對快遞員來說,賠錢是家常便飯。大多數時候是由于丟件,但也有別的情況。當時高樓金有個快遞小哥,在小區里三輪車開得太快,避讓一個孕婦時,車子側翻摔倒,前擋風罩脫落碎裂。孕婦雖然沒被撞到,但受了驚嚇。他修車加賠償人家花了近2000元,當即就決定辭職不干了。
我還記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說“我已經不干了”時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驚嚇可能不比那個孕婦小。我聽說過的金額最大也最離奇的賠償,發生在臨河里路的方恒東景小區。一個快遞員在把快件塞進消防栓時,水管或接頭被他弄壞了,水噴出來灌進電梯井里,導致電機損壞,最后賠了三萬元錢。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見的。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一般來說,只有在發工資的時候,我才會感覺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說客戶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頭表達謝意的時候——雖說那種時候我也很欣慰。
| 02上廁所都算到成本里
我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在我們周圍一帶,快遞員和送餐員在不包吃住的情況下,平均工資是7000元左右。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決定的,是長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場行情。低于這個報酬,勞動力就會流動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工種。
那么按照我每個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元。這就是我的勞動價值——我避免用“身價”這個詞。我每天工作11個小時,其中早上到站點后卸貨、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去往各小區的路上總共花去一個小時,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
那么剩下用來派件的9個小時里,我每個小時就得產出30元,平均每分鐘產出0.5元。反過來看,這就是我的時間成本。我派一個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須每四分鐘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于虧本。如果達不到,我就該考慮換一份工作了。
漸漸地,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比如說,因為我的每分鐘值0.5元,所以我小個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我花費了兩分鐘時間。
我吃一頓午飯要花20分鐘——其中10分鐘用于等餐——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加起來就是25元,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
在派件的時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約有一半的住宅沒人——我花一分鐘打個電話,除支出0.1元的話費外,還付出了0.5元的時間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遞柜,我將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而且往快遞柜里放一個快件,平均還要付0.4元,那么這筆買賣我就虧本了。
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將虧損更多——不僅打了電話,還將付出雙倍的勞動時間。這些還只是順利的情況。假如電話沒人接聽,我將在等待中白白浪費一分鐘,也就是0.5元。還有的電話打通后就很難掛掉,客戶百折不撓地提出各種我滿足不了的要求。
有時打完一個電話后,花去的時間成本已經超過了派件費,可這快件還在手上沒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還是在玉蘭灣,我在客戶預約的時間上門取一件唯品會的退貨,但客戶并不在家。電話接通后,是一個親切的中年女聲,她說要晚上七點后才到家,讓我到時再過來。不過七點后我已經下班了,所以我讓她把預約時間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說,明天也是七點后到家,她每天都是這個時間。
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建議您把退貨帶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訴我,她在醫院上班,工作的時候不方便處理私事。像這種情況,她只能自己把退貨寄回了,唯品會的上門攬退不支持夜間預約。
不過那樣她會有點兒麻煩,因為玉蘭灣的快遞員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門收件。但S公司的運費遠高于平臺補償的10元,大多數人并不愿意發S公司。而發其他快遞,她要自己帶去快遞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費這個勁兒。
相比而言,在電話里動員我是更省心的解決辦法。何況她顯然是個樂于溝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爭取就有可能。
在我拒絕了她的幾個提議后,她問我能不能下了班吃過晚飯之后,到玉蘭灣散步,順便把她的退貨取了。她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態度,措辭很得體,語調溫婉,富有感染力,簡直無可挑剔。
不過,晚上到她的小區去并不像她說的那么詩情畫意,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喇叭、廢氣、紅綠燈……誰會選擇散這么個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3.5元,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3.5元,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
或許她自己是個工作狂,義無反顧地愿意為工作付出和犧牲,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她認為我理應和她一樣。
可是我的覺悟沒有達到她的水平,而且我還想反過來建議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飯出來散個步,順便找個快遞站把退貨寄掉。當然我沒有真的這么說,我隨便找了個理由拒絕了她。
后來我還給她送過幾次貨,面對面的時候她仍然很禮貌,絲毫沒有因為我曾拒絕過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碼沒讓我感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