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的“雙11”,各大電商平臺掀起“保衛戰”——
京東把主題定為“真便宜”,拼多多提出“天天真低價”,淘寶天貓則直接喊出“全網最低價”。
消費者,卻很是“高冷”,仿佛當年的“剁手少年”一個個“長成了大人模樣”。一項媒體發起的“‘雙11’是否會囤貨”投票顯示,5900余名參與者中有42%選擇“不買”,有33%的人表示“看情況”。
反觀海外,各大社交媒體上人們早已摩拳擦掌。從老牌的亞馬遜、速賣通,到后起之秀Temu、TikTok Shop,不管海外電商平臺,還是中國“出海”電商平臺,伴隨“雙11”“黑五”等大促活動拉開序幕,消費熱潮接踵而至。以Temu數據為例,中金預測受大促影響,該平臺全年商品交易總額或達180億美元,遠超預期的150億美元。
梳理這些數得上名號的電商平臺,中國賣家毫無疑問占據了供應鏈的半壁江山。新經濟形勢和新消費趨勢下,跨境電商會是穿越周期的力量嗎?“雙11”之際,我們深入杭州家紡服裝、義烏小商品、慈溪小家電等產業帶,窺見另一處“戰場”。
浪潮和暗流
除了汽車,我們很難再找出一條賽道,能比過去這些年的跨境電商更火熱、更刺激。“銷售額10倍增長”“幾個月賺夠花一輩子的錢”“干了一年,全款在深圳買了房”……這些,還真不是段子,而是現實。
身處跨境電商之都杭州,浙江家友高科創始人成龍是親歷者和見證者。2015年,他回建德接手父親的工廠,嘗試過外貿,改造過產品線,但一直起色不大,“2021年初我們注冊現在的公司,專做家紡、家居、小家電等全品類跨境電商,當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去年突破2.5億元,今年預計近7億元。”
而原先自家的工廠,如今變為供應商之一,今年營收已達9000萬元。

近日,杭州蕭山國際機場開通墨西哥全貨機航線,滿足跨境電商貨物出口拉美需求。譚申捷 攝
那么,傳統外貿和跨境電商,究竟有何區別?
成龍告訴記者,通過傳統外貿方式把貨物賣到國外,首先要經過國內貿易公司,其次是國外貿易公司,接著是品牌商,最后才是他們入駐的超市、門店等,環節多、流程長,并且貿易公司和品牌商的能力會極大影響出貨量。跨境電商,則是賣家直接入駐亞馬遜、沃爾瑪等電商平臺,對接海外品牌商,甚至直面消費者。
一句話總結,就是“拒絕中間商賺差價”。
伴隨理念變革以及海外倉等新模式崛起,尤其是疫情初期線上經濟需求大爆炸,跨境電商“一夜爆火”。
看供應端。以杭州為例,2015年獲批設立全國首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到2019年,全市跨境電商出口額95.48億美元,而2022年,跨境電商規模已經躍升至1203.33億元。跨境電商賣家數,則從2015年的200多家,增長到2022年的55381家,其中規模億元以上企業157家。
全球市場的風向標——義烏,經工商登記注冊的57萬余戶電商主體中,40%以上從事跨境業務。義烏市場發展委黨組成員、電子商務科科長喻中華介紹,從2017年至2021年,當地跨境電商交易額連續增長超過15%,2022年突破千億大關,達到1083.5億元。2022年底時,義烏在各大第三方跨境電商平臺上用戶數超18萬個,僅阿里速賣通和國際站平臺,2022年新增跨境電商主體超2200家。

義烏綜保區物流繁忙。共享聯盟·義烏 吳峰宇 攝
再看平臺端。除了較早布局的速賣通,從廣州低調起家SHEIN(希音),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打敗ZARA、席卷全球、成為世界快消品市場領頭羊,去年估值達到1000億美元。
拼多多旗下平臺Temu,于2022年9月橫空出世。上線一個半月,就超越亞馬遜,登頂美國購物應用下載排行榜。眼下,已“搶灘”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馬來西亞等地。
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 Shop,則如一枚水雷,以直播和短視頻帶貨模式,“炸開”了后疫情時代的全球電商市場。第三方數據分析平臺統計,僅TikTok Shop美國站,今年10月,已提交入駐小店數量達25萬家,較9月增加近70%。
然而,似乎是印證“福兮禍所伏”,從去年下半年至今,全球多數經濟體出現下行趨勢,原料上漲等加劇成本壓力,通貨膨脹等帶來消費變局,跨境電商賽道同樣受到沖擊。
與此同時,國際形勢變化、電商平臺紛爭等,也帶來新的變數。
“從歐美看,這兩年市場整體是萎縮的。特別是中產消費降級,對一些行業的打擊是很致命的,像Soft Surroundings、Wearhouse等不少美國連鎖零售企業破產就是印證。”2018年從傳統外貿企業轉型做跨境電商,身處杭州臨平新城的杰西亞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格青看過行業風風雨雨,他預感到,當前跨境電商正從1.0時代邁入2.0時代,大洗牌隨時將至。
大風勁吹,海面上是浪潮,海面下是急流。
藍海和紅海
至今,成龍仍對亞馬遜的“封店潮”記憶猶新。
2021年5月,亞馬遜平臺利用《賣家行為準則》等格式條款,一夜之間關閉5萬余家店鋪,凍結資產超千億元。其中,所涉店鋪大多為中國賣家。
成龍告訴記者,亞馬遜平臺的盈利來源之一是收取店鋪傭金,由此規定一家公司開一家店。但實際上,一家公司可能有多個不同品牌,因而常會采取一家店鋪對應一個品牌模式,“亞馬遜認為這些店鋪是違規的,進行封號關店處理。倘若之前在亞馬遜倉庫放了價值300萬元的貨,光退貨費用就要300萬元,從美國運回中國又要一筆費用,而且平臺賬號又禁用了,即使把貨賣掉,錢也拿不出來。對很多運營了數年的品牌和賣家來說,可謂‘竹籃打水一場空’。”
除了老牌平臺上的變數,新平臺打出的招數,也讓賣家們感嘆“亂花漸欲迷人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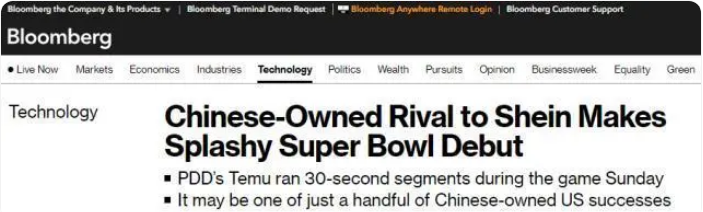
國外媒體關于中國電商平臺“出海”的報道。
比如Temu,一入美國,就掀起“狂風暴雨”。從WhatsApp到Tik Tok再到X(原Twitter),在各大海外社交平臺上,人們可能都收到過這樣一條信息或評論,“能不能下載這個軟件,幫我拿到這些免費禮物”。
這一幕,讓記者恍惚回到了那年被拼多多“砍一刀”鏈接“支配”的時刻。
相比亞馬遜和速賣通,Temu幾乎都不算典型的跨境電商平臺,不是B2C(企業對消費者),也不是C2C(個人對個人),而是C2M(從消費者到生產者)——采用“全托管”模式,打造極致的低價,進而征服國際市場。
這股來自東方的神秘力量,甚至“嚇”得亞馬遜將它直接剔除出了比價系統。繼Temu之后,Lazada、Shopee、速賣通等跨境電商平臺陸續推出全托管服務。
“除了提供貨品、備貨入倉,其他一切的定價、銷售、營銷、營銷、物流配送、售后等環節都由平臺包辦。”采訪中,義烏一家電商公司負責人史陽說,此前Temu在義烏進行地推時,他的生意遭遇瓶頸,急需一個轉折點,便決定加入平臺成為第一批賣家。
起初,單量并不大,每天50多單。很快,Temu在“美國春晚”NFL超級碗賽事上打出廣告:shop like a billionaire(像億萬富翁那樣購物),并火速出圈。史陽的產品開始爆單,日均訂單瘋漲到4000單。
“‘小二’天天來催貨入倉,工廠縫紉機都踩得冒煙了,仍然跟不上銷售速度。”史陽感慨,當時,他就賣一款地毯,價格約8美元,一天賺20萬元人民幣不是夢。
對另一位電商企業負責人李爭峰來說,之所以選擇全托管模式,是因他此前專注國內市場,在京東平臺運營5家店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成本,對歐美市場的消費需求也不是特別了解,“平臺幫助省去了繁瑣的運營環節,對于我們這樣想做跨境電商試試水的公司,有很大吸引力。”

流水線上的跨境包裹。共享聯盟·義烏 吳峰宇 攝
但眼下,平臺還在推廣期,給了賣家一定的流量和利潤傾斜。一旦像亞馬遜一樣改變規則,訂單和銷售還能持續嗎?一旦適應了當“甩手掌柜”,賣家們還會有運營產品的能力嗎?
對此,義烏跨境電商協會會長徐儼認為,這些新平臺、新模式,降低了中國制造和中國品牌“出海”的門檻,減少賣家投入和成本,同時可以幫助企業迅速挖掘爆款,提升產品銷售額,但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企業話語權和對數據的敏感度和掌控度。
這,有可能是一把雙刃劍。
同樣的觀點,出現在今年5月Temu在慈溪的小家電招商會活動上。一位剃須刀生產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為了追求極致的性價比,平臺制定了一系列規則,比如,供貨價要比1688上同款商品價格更低,此外還有所謂“賽馬機制”,同一款商品不管有多少賣家報價,只會選擇價格最低的那一個。這無疑會刺激價格戰,壓縮制造業生存空間。“可能會有企業為了低價犧牲質量,最后造成劣幣驅除良幣。”該負責人說。
然而,猶疑也好,已經躬身入局也好,面向風浪,唯一的辦法是應對。
變局和應變
“滴,滴,滴!”掃碼槍聲音不停,一個個包裹飛速在傳送臺分撥。
距離“黑五”還有一段時間,但隨著“雙11”付尾款活動正式開啟,義烏保稅物流中心內的跨境電商企業們已經開始備貨。庫區燈火通明、人聲鼎沸,月臺堆滿包裹、蓄勢待發。
面向年終大促,國內電商平臺開啟“低價戰”,跨境電商平臺們則打響了一場“時效戰”。
據速賣通相關負責人介紹,9月26日,他們聯合菜鳥上線了“全球5日達”國際快遞快線產品,首批落地英國、西班牙、荷蘭等國,10月25日,又和菜鳥一起發布了“六大跨境物流保障”,通過航空干線加頻加密、跨境倉庫擴容等,提升“5日達”達成率和服務質量,“最終目標,是想打造史上最快海外‘雙11’”

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國際貨運站。譚申捷 攝
作為跨境電商中心地段,義烏不僅要將本地貨運出去,還要接收來自華東、華南各地貨物,再轉運出國,物流體系是否完善顯得至關重要。
“以東南亞為例,Shopee、Lazada兩大主要平臺都在義烏布局了集貨倉,日均出貨量分別超20噸、10噸。但此前我們缺乏相對便捷的出貨通道,貨物要先到杭州,再搭乘貨機,有時甚至要從廣州、深圳等地轉運。”義烏市市場發展委相關負責人,為提升出口時效,今年他們開展招商引資,眼下僅義烏到大阪的航班一周就有5趟,機上貨物70%以上為跨境電商貨物。
那么,面對跨境電商變局,賣家們又如何應對?采訪中,記者聽到同一個關鍵詞“產品”。
史陽介紹,為了趕上“雙11”,他們研發了多款新品,爭取“一炮打響”。
在杰西亞,除了有8位設計師分析歐美市場流行趨勢,并進行產品風格分項研究,還有專門的產品規劃部門、產品調研部門等負責用戶畫像、了解產品市場容量等。
“盡管消費在下行,但海外市場的消費者有非常多樣性的需求,而國外家居零售企業更看重主流市場和大眾需求,追求標準化、規模化。這20%的細分市場,對我們跨境電商企業來說,就是機遇。”鄭格青預計,“黑五”期間,公司銷量能達日常的3倍左右。
“做實業也好,做電商也好,核心競爭力都在產品。”成龍說,以家紡為例,生產面料、制作毯子這些都是最初級的,是隨時可以被別人取代的,因此必須要做與眾不同的產品,比如可以抗菌的毯子、可以根據姿勢提供睡眠建議的床墊等。
紅海之間,也有藍海。有時,大環境的變化,一個個體、一家企業很難抵抗,但在變化之中升級,在競爭之中求異,這就是生意之道,也是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