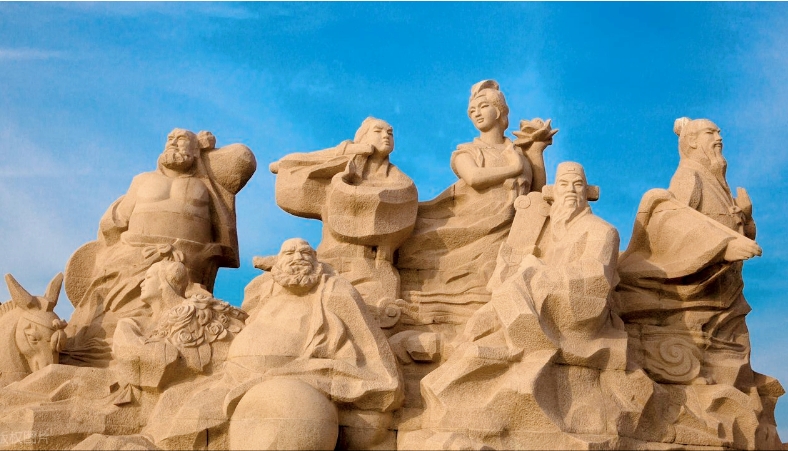在全國人民心中,義烏是最會做小商品生意的地方。
然而,少有人知道在北方山東,藏著一個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
這座城市就是山東臨沂。
與義烏從古至今傳承的經商文化不同,山東臨沂和大多數普通城市一樣,一直傳承的是刻在骨子里的農耕文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山東臨沂迅速完成了從農耕文化到經商文化的蛻變。
臨沂僅用20年的時間發展為“中國大集”,成為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僅用30年,又躍升為中國的“物流之都”,至今仍在不斷升級。
有人這么形容臨沂的批發市場之大:如果在每個店鋪只逛一分鐘,不喝不吃不休息也得近50天才能逛完整個批發市場。
據統計,去年,臨沂批發市場年總交易額僅比義烏低80億元,為6605億元,而物流交易總額更是突破萬億大關,為1.0074萬億元。
這讓人不禁好奇,臨沂是如何完成從農業經濟到商業經濟的大步伐躍遷?
一
改革開放前,臨沂可謂是交通閉塞,舟車不通的農業地區。
改革開放后,隨著地攤商業模式的興起,當地農民自發在人流量大的城區擺攤售賣貨物,形成了集市。
由于這樣的集市一周才出現一次,再加上集市比較混亂,難以滿足需求。
當地部門主動學習南方的商業模式,于1981年建立起第一個正規市場——“西郊大棚”,主營百貨零售。
隨著西郊大棚首個集市的建立,這里很快就得到許多南來北往的商人青睞,并依次進駐臨沂,為市場注入了活力。
攤位不夠,外地商人就在市場外擺攤,甚至擺到了旅館的院子里。
原本一周一次的集市,最后變為天天集市,人來人往,絡繹不絕,零售漸漸供不應求,市場的很多商人干脆搞起了批發。
到1986年,臨沂正式進入市場批發時期,當地很多村子和工商部門合作,先后辦起了紡織品,五金鋼材等眾多品類的批發市場。
隨著市場的發展,2005年,臨沂的專業市場版圖已擴展至68處,成為數十萬人的就業引擎。

市場日均吸引客流超30萬人次,年成交額突破400億元大關。
在當地部門對批發品類不重復的嚴格規定下,如今臨沂已經發展到136處專業批發市場,6.22萬多家門店,其中包含了27大類商品。
換句話說,生活中所有的需求品都能在這里找到。
有人舉例,在臨沂的批發市場,東拼西湊零件,都能組裝一輛汽車。
品類繁多吸引顧客,顧客眾多吸引商家,臨沂以滾雪球的方式一路發展到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被稱為“中國大集”。
有龐大的批發市場,自然衍生出另一個行業——物流。
進入21世紀,當地部門認識到物流是提高交易效率的關鍵,緊跟時代思路,大力改善、升級物流。
2008年,大型物流園區啟動建設。
幸運的是,臨沂恰好位于中國東部京津冀經濟圈的中心,北連距離558公里的北京,南連524公里的上海,像一根扁擔的支點一樣,挑起了南北兩地的經濟。
作為東西南北的樞紐,臨沂無論通向哪里都非常方便,臨沂很快發展到3000 多條公路運輸路線,能直達全國所有縣級以上城市。
另外,大集促進了物流的低成本,相比國內其他地方,物流價格要平均低于30%。
以一張臺球案為例,從上海直接發快遞到新疆,運費需要320元,用時15天,然而從上海發到臨沂,再從臨沂發到新疆,運費只需120元,用時竟減少到10天。
憑借地理優勢和大集市的活力,2010年,臨沂榮膺“中國物流之都”。
回望臨沂的發展,臨沂正是憑借大膽嘗試,抓住了商業先機,實現了一步領先,步步領先。
二
沒誰會一如既往輝煌,臨沂深知時代變化帶來的影響,也并未因抓住了一次的時代機會而選擇一勞永逸。
在時代潮流的變遷中,臨沂也要面對不確定的壓力。
一方面,隨著全國各地交通的改善,臨沂要面臨周邊城市打造批發市場的行業競爭壓力,另一方面,臨沂要面臨電商沖擊統批發市場的壓力。
為了趕上商業時代潮流,當地部門極力推動大集市的轉型,從線下交易轉戰為線上交易。
于是,急于變化的眾多商家也向電商轉型,畢竟轉型到一個新領域,市場經濟并沒有達到新的突破,只是不溫不火。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20年的疫情,反而將臨沂推向另一個新行業的金字塔端。
為了應對疫情帶來的危機,眾多商家一窩蜂似的扎入了直播帶貨行業。
臨沂本就有較大規模的市場貨源,這猶如給直播帶貨注入了活水,吸引了一大批主播駐扎臨沂,就此臨沂又被冠以新的名頭“直播電商之城”。

不到一年時間,直播帶貨就帶來了超過100億元的總交易額,竟占臨沂電商總交易額的50%之多。
到了2022年,直播帶貨交易額已超500億元,位居全國地級市首位。
如此佳績,自然離不開龐大的直播群體支撐。
據統計,僅在某手、某音兩大平臺注冊的臨沂用戶就超過1460萬。
其中,擁有一百萬以上粉絲的帶貨主播用戶就超過500人,其中擁有500萬以上的粉絲占25位,擁有1000萬以上粉絲的占6位,年銷售額超過五千萬的就有29位。
除了轉型電商行業以外,臨沂在市場規模擴大、物流升級方面從未停下腳步。
臨沂深知商品全球化是當下的潮流,為此開通多條到達全球的貨運通道:
27條中歐班列、4條通達歐亞的TIR(國際公路運輸)線路、340條連接周邊7大港口的近遠洋航線等。
自從臨沂開通跨境路線,步入國際貿易后,臨沂的大集深受亞歐大陸的喜愛。
這也為臨沂帶來新的機會,國家把臨沂列入了跨境電商試點。
借此機會,臨沂迅速擴大規模,跨境電商一路增加到20家,覆蓋到出口商品的全品類,并建設了40處海外倉。
為了贏得出海先機,臨沂每年都會組織千家企業組團跨境,到20多個國家搞促銷,拿訂單,2024年更是完成61億的交易額。
努力趕路的人從不被辜負,2024年,臨沂的進出口交易總額達到了1691.9億元,其中跨境電商占到280億元,比2023提升了30%。
無論面臨什么樣的時代風潮,臨沂的發展一直在突破的路上。
三
有人可能會說,臨沂能有如此成就,是地理位置占據了優勢。
其實,臨沂有地理優勢沒錯,但最關鍵的還是人為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當地政府相關部門。
改革開放初,還是一個對“投機倒把”的商業交易概念比較模糊的年代。
很多地方寧可選擇保守求穩發展,也不愿意以身試險,而臨沂能選擇大膽嘗試,可見當地的魄力和見識非凡。

其次,當地政府提出的“一品一市”的審批原則。
明顯,這樣的原則就會讓不同品類商家協同共贏,少了相互競爭,免了市場的惡性內卷。
相反,“一品一市”的原則,既吸引了不同類商家的加入,也一站式地解決了客戶需求,節省了客戶時間,如此以往,提升了客流量,又吸引了商家,隨之市場的雪球越滾越大。
在那個年代,臨沂能有如此長遠的商業見識本身就是一種難能可貴。
最后,就是臨沂政府的包容與支持。
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地商戶擺小攤時,臨沂相關監管部門不僅沒有驅趕,還想著如何能讓群眾規范經營,并投資建設了西郊大棚市場;
據一個義務商戶陳文彪的描述,1985年跟隨舅舅在“西郊大棚”租下了攤位賣紐扣,當地政府不僅不為難外地人,還給私人經濟和國有經濟一樣的資源和支持。
2020年,陳文彪遇到資金困難,在沒有擔保的情況下,銀行僅僅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為他貸了200萬元,應對了他的當下之急;
據一位叫朱建紅的描述,2021年,他的快遞公司因用人不當,損失了2000多萬元,當自己在低谷徘徊之際,當地政府提供了超過自己想象的支持。
他原本擔心,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可能打不贏官司,但令他沒想到的是,相關部門了解真實情況后,依法處理,并幫助他的公司渡過難關。
2022年,有關部門還將一名稅務局三級調研員派駐到他的公司提供駐企服務,方便他第一時間能夠咨詢到稅收問題。
臨沂的態度就是管好該管的,以“服務”為核心,市場能解決的就放手支持,市場不能解決的,政府就補位提供支持。
同時也道出一個真相,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離不開當地部門的支撐。
臨沂的發展證明,最先進的智慧,永遠服務于最樸素的生存。
從推車送軍糧的老支前,到開TIR卡車的司機;從納鞋底的紅嫂,到產業園的女工;變的是工具,不變的是那句沂蒙山的誓言:
“只要路在腳下,就能把家國扛向遠方。”